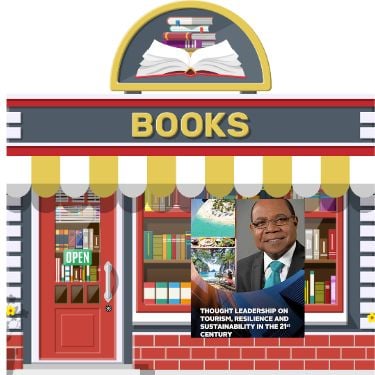西奈山ED,地球上的地狱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与纽约市西奈山和纽约大学朗格尼分校两家主要医疗机构的急诊室进行了近距离接触。 因为西奈山以但丁的地狱景象为模型,所以我不会徘徊在等待任何有勇气进入这个设施的人的数千种恐怖之中。
从数百名(也许是数千名)等待医疗救治的病人,他们堆放在轮床上,停得比罐头里的沙丁鱼靠得更近,再到病得很重的人呕吐到便盆里,肺部顶部疼痛地尖叫,几乎每个人都被忽视了。由少数可以在西奈山救治伤病员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负责。
医生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找到的! 忘记《芝加哥医学》和《实习医生格蕾》中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医生/护士的形象吧! 我们一直以来对医生、护士和医院管理人员的看法纯属虚构,真实性不如戈尔迪·洛克斯和三只熊。
在西奈山,卫生是一个专门出现在字典中的概念。 最基本的用品,从卫生纸到手巾和女性卫生用品——所有用品都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如果有的话)。 医生快速飞过——通过喊叫病人的名字来寻找病人,并等待病人或受伤的人举手表明自己的身份。 有时,医务人员必须爬过并绕过堆叠的轮床,因为他们要寻找的人位于后四排,而且他们必须在无数其他拼命寻求与医生或护士交谈的患者中摸索(想想炸弹爆炸后伤亡惨重的战区,每个士兵都拼命寻求关注)。 我参观过新兴国家的医院,西奈山的医疗服务水平低于最不发达的加勒比国家、印度或南非。
患者数小时甚至数天只能依靠自己的设备,没有食物、水、卫生用品、药物,也无法更新自己的病情,还要长时间步行去厕所。 如果您没有手机,您可能会忘记与任何人联系。 如果您没有充电器和备用电源,请忘记 Wi-Fi 和电话接入,因为轮床附近没有充电站,而且计算机终端仅供工作人员使用。
经过近10个小时的无数不知名的医务人员的测试和戳戳后,我终于被告知,由于我的病情严重,我将被送进医院病床。 几个小时过去了,唯一的动作是一名护士将我的轮床移得离其他人更近,因为急诊室病人数量激增,而且没有更多的可用空间。 忘记新冠肺炎预防措施的 6 英尺距离,忘记更新的 HVAC 系统, Covid 在西奈半岛的紧急环境中,这甚至不是事后才想到的。 当我终于找到一位愿意与我交谈(并且不再盯着电脑屏幕)的护士时,我被告知我可以等待长达 72 小时才能真正在医院找到一张床位(这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确实尝试联系将我转介到西奈急诊室的胃病医生,但他没有回复电子邮件,也没有其他方式联系他。
我病得太重、太饿、太脏、太生气,无法留在西奈半岛——所以我出院了,决心在家解决我的医疗问题。 我不得不(再次)找到我的护士并说服他将视线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告诉他我要离开。 他联系了胃肠科的一位医生,因为出院前需要准备文件。 几分钟/几小时后,一位医生终于来到了我的轮床前。 有一次他询问我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他想知道我为什么在急诊室以及我的医生的名字! 这位“医生”不知道我是谁,也不在乎。 这家伙唯一的兴趣是什么? 签署文件,让护士取出我的静脉注射管,然后送我上路。
我在西奈急诊室幸存下来,但噩梦的记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个人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前往西奈山寻求医疗紧急情况。
幸运的是,我能够叫到一辆出租车(我的手机上没有剩余电量,也没有医院地址,所以 Uber 和 Lyft 是不可能的)。 我回到家,洗了个澡,试图睡觉,当我醒来时,试图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
帐户继续
不幸的是,我并没有走上奇迹般治愈或立即康复的道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病情逐渐恶化。 凭借顽强的毅力,我突破了纽约大学兰格尼分校的医生封锁,终于找到了愿意接受几天/几周而不是未来几个月的新患者预约的医生。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位老年学医生,他沉着地安排了超声检查,这次测试验证了我的病情,为其他医生提供了解决方案的途径。 这并不是一帆风顺。